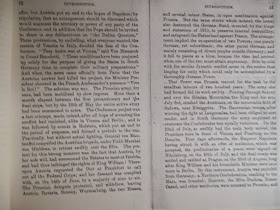美國無風起浪 港陷烏克蘭撕裂
撰文: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欄名:政改之爭
香港經濟日報 8/29/2014 袁彌昌 專欄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c32c1408-f240-4d65-b6c4-a7bf7c9cd959-252290
在香港政改的關鍵時刻,美國最新一期《外交事務》期刊的封面主題是「看看美國:衰敗與失效之地」。當中有兩篇文章最能引起筆者的興趣:
第一篇是曾主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作者)的〈衰敗中的美國〉,內容不言自喻,分析目前美國政治失效的原因,只是由福山道出卻極具諷刺性;
第二篇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John Mearsheimer(下稱米氏)的〈為何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以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烏克蘭危機,指出該危機是由美國及其盟友挑起的。
兩篇文章都與香港前途息息相關,不過筆者在這篇只集中討論後者。
烏靠俄天然氣 港不能缺東江水
今年2月烏克蘭革命爆發後,西方有多篇文章剖析了革命成因和烏克蘭國內狀況,當中有不少現象與情況,與同處於政爭和內部撕裂漩渦之中的香港,相當相似。這 讓我們可以借鑑烏克蘭危機這個更具國際性、影響更廣泛的個案,了解在漩渦之中的國家/地方(烏克蘭、香港),以及爭奪的大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動 機、策略及互動。
作為地緣政治的基本概念,任何大國對於在其本土周邊的潛在威脅都特別敏感:絕不容忍其他遠方大國在本國附近駐軍,或容許鄰近國家加入敵對的軍事同盟。這固 然屬國家安全問題,不過亦引伸出大國需要以政治、經濟等手段,持續地維持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以防止他們落入敵方陣營。
因此,即使香港並非一主權國家,但中國對之施以影響力的做法,幾乎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如出一轍。政治上,俄羅斯固然要扶植親俄政黨,也與該國的官僚機構有 一定聯繫,希望盡量以和平的方式來穩住烏克蘭。在其他範疇,俄羅斯企業則大舉進軍烏克蘭的核能業、電訊業(特別是流動電訊)及銀行業,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和 佔有率。俄羅斯當然亦不忘控制烏國的傳媒,只是當地媒體也懂得兩面下注,而在烏國可接收的俄羅斯媒體則一味發放反西方反美信息,因而效果不彰。
不得不提的,是烏克蘭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俄國供氣佔烏國的消費量近六成,但至今仍未找到可靠的替代來源,這與香港依賴國內東江水及糧食供應有一定的可比較性。
烏成攻俄跳板 港有亡共威脅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有對俄羅斯不可或缺的價值,例如位處克里米亞半島塞凡堡的俄國黑海艦隊基地,維繫着俄國的海軍實力,重要性有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 對大陸的作用。而一直觸動着普京的神經的,是烏克蘭遼闊的平原,在歷史中一直是敵國進攻俄羅斯的跳板,經歷過拿破崙、德皇及希特拉等的侵略,任何俄國領袖 已不可能再接受烏國受到敵對勢力控制,這一點跟香港有如一條「意識形態高速公路」,能將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迅速傳往內地,威脅中共的統治相若,絕不能將 之拱手相讓予敵人,卻因而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另一邊廂,如上文和米氏一文所言,西方最管用的板斧,來來去去都是其「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伎倆——以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改變和操控目標民眾的想法與行為,但背後自然少不了金錢的助力。
美國負責歐洲及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毫不諱言,自1991年蘇聯解體起,美國在烏克蘭已投放了超過50億美元,以助之得到「它應得的未來」,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它在烏國資助了超過60個「提倡公民社會」的項目,其總裁Carl Gershman亦不諱言烏國是「最大的獎品」,並明言若烏國加入歐洲,將加速俄羅斯意識形態的潰散。
美煽動烏反俄 放水明目張膽
大家試想想,假如香港是一主權國家,那麼美國早就像在烏克蘭般大灑金錢,明目張膽地煽風點火,將它發展為反中反共基地,直指國內,不用像現時閃閃縮縮地透過黎智英資助香港的民主活動了。由此可見,即使以往美國表態支持香港回歸,但它只要有空子就會鑽,不會錯過任何機會。
俄羅斯早就對北約及歐盟東擴起戒心,但要到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及其他顏色革命爆發後,才清楚美國葫蘆裏賣甚麼藥。2008年,北約考慮將格魯吉亞和 烏克蘭納入北約,其間普京已明確表示「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它將不復存在」,以表明他的決心,可是北約仍聲明兩國將加入,這直接導致了同年的俄羅斯——格 魯吉亞戰爭。
之不過,格魯吉亞的戰敗及其兩大片土地被割,並沒有令北約公開聲明放棄納入格魯吉亞及烏克蘭,北約反而在翌年繼續東擴,將阿爾巴尼亞及克羅地亞納入陣營。 北約的擴張,連圍堵政策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也看不過眼,指「是個可悲的錯誤,根本沒有理由這樣做」。
換言之,俄羅斯已多次警告美國,美國就是不聽,這也是為何米氏認為普京往後的行為,包括佔領克里米亞,純粹是防守性,而非攻擊性的主要理據。事實上,2月 的烏克蘭革命,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是經合法渠道取得政權的,但美國與歐盟卻煽動烏克蘭反對派,以非法手段推翻亞努科維奇,你說普京怎會不光火?這與香港開 始有人拒絕認同「少數服從多數」,主張公民抗命,程度有差異,但本質上是相同的。
愛挑撥離間 出事後袖手旁觀
再者,美國在革命中的介入是明顯的:紐蘭與美國前總統候選人,現任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竟親自參加了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大家可想像他們來港參與示威)!
革命發生後,副總統拜登不忘鼓勵一眾烏國議員,說「這是達成原來橙色革命目標的第二次機會」。中情局局長亦連忙提升與烏政府的安全合作,這些毫無疑問是西方的挑釁性舉措,但可恥的是,美國心知自己鞭長莫及,根本沒有意思出兵支援烏克蘭。
「真普選」若到手 港撕裂更容易
簡單來說,在格魯吉亞、烏克蘭或香港也好,美國就是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引誘和挑撥他們的反對派領袖和人民,即使他們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亦然,這在任何有直選的地方也幾乎必定會成功——故取得所謂「真普選」,反而會令香港更易走上烏克蘭的撕裂之路。
此外,不難發現美國其實最喜歡用反對派自己的損失(如普選),來挑起他們對目標對象(俄羅斯/中國)的敵意和怒火,但到出問題時,她卻不會理你的死活——如格魯吉亞因戰爭而兩地被割,西方卻連手指頭也沒有動一下;烏克蘭丟失了克里米亞,情況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目前美國在香港所採用的「非暴力鬥爭」這一套卻更卑劣:美國連錢也不願多花,要反對派自己動手,令美國毋須親自介入,變相叫他們自生自滅,如果見勢色不對就改打持久戰,搞「不合作運動」,她自己則靜觀其變。
話說回來,雖然中央對香港普選的國家安全憂慮完全成立,但筆者也認為,將普選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鈎,對港人來說很難接受:一則中央在普選問題上已應允了港 人,二則是大多數港人仍未習慣以此角度思考問題。之不過,「國家安全」這層面的考慮,在「後佔中」時代必然會繼續存在,港人對此必須有更深刻的理解,不要 奢望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
欄名:政改之爭
香港經濟日報 8/29/2014 袁彌昌 專欄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c32c1408-f240-4d65-b6c4-a7bf7c9cd959-252290
在香港政改的關鍵時刻,美國最新一期《外交事務》期刊的封面主題是「看看美國:衰敗與失效之地」。當中有兩篇文章最能引起筆者的興趣:
第一篇是曾主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作者)的〈衰敗中的美國〉,內容不言自喻,分析目前美國政治失效的原因,只是由福山道出卻極具諷刺性;
第二篇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John Mearsheimer(下稱米氏)的〈為何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以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烏克蘭危機,指出該危機是由美國及其盟友挑起的。
兩篇文章都與香港前途息息相關,不過筆者在這篇只集中討論後者。
烏靠俄天然氣 港不能缺東江水
今年2月烏克蘭革命爆發後,西方有多篇文章剖析了革命成因和烏克蘭國內狀況,當中有不少現象與情況,與同處於政爭和內部撕裂漩渦之中的香港,相當相似。這 讓我們可以借鑑烏克蘭危機這個更具國際性、影響更廣泛的個案,了解在漩渦之中的國家/地方(烏克蘭、香港),以及爭奪的大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動 機、策略及互動。
作為地緣政治的基本概念,任何大國對於在其本土周邊的潛在威脅都特別敏感:絕不容忍其他遠方大國在本國附近駐軍,或容許鄰近國家加入敵對的軍事同盟。這固 然屬國家安全問題,不過亦引伸出大國需要以政治、經濟等手段,持續地維持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以防止他們落入敵方陣營。
因此,即使香港並非一主權國家,但中國對之施以影響力的做法,幾乎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如出一轍。政治上,俄羅斯固然要扶植親俄政黨,也與該國的官僚機構有 一定聯繫,希望盡量以和平的方式來穩住烏克蘭。在其他範疇,俄羅斯企業則大舉進軍烏克蘭的核能業、電訊業(特別是流動電訊)及銀行業,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和 佔有率。俄羅斯當然亦不忘控制烏國的傳媒,只是當地媒體也懂得兩面下注,而在烏國可接收的俄羅斯媒體則一味發放反西方反美信息,因而效果不彰。
不得不提的,是烏克蘭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俄國供氣佔烏國的消費量近六成,但至今仍未找到可靠的替代來源,這與香港依賴國內東江水及糧食供應有一定的可比較性。
烏成攻俄跳板 港有亡共威脅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有對俄羅斯不可或缺的價值,例如位處克里米亞半島塞凡堡的俄國黑海艦隊基地,維繫着俄國的海軍實力,重要性有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 對大陸的作用。而一直觸動着普京的神經的,是烏克蘭遼闊的平原,在歷史中一直是敵國進攻俄羅斯的跳板,經歷過拿破崙、德皇及希特拉等的侵略,任何俄國領袖 已不可能再接受烏國受到敵對勢力控制,這一點跟香港有如一條「意識形態高速公路」,能將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迅速傳往內地,威脅中共的統治相若,絕不能將 之拱手相讓予敵人,卻因而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另一邊廂,如上文和米氏一文所言,西方最管用的板斧,來來去去都是其「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伎倆——以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改變和操控目標民眾的想法與行為,但背後自然少不了金錢的助力。
美國負責歐洲及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毫不諱言,自1991年蘇聯解體起,美國在烏克蘭已投放了超過50億美元,以助之得到「它應得的未來」,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它在烏國資助了超過60個「提倡公民社會」的項目,其總裁Carl Gershman亦不諱言烏國是「最大的獎品」,並明言若烏國加入歐洲,將加速俄羅斯意識形態的潰散。
美煽動烏反俄 放水明目張膽
大家試想想,假如香港是一主權國家,那麼美國早就像在烏克蘭般大灑金錢,明目張膽地煽風點火,將它發展為反中反共基地,直指國內,不用像現時閃閃縮縮地透過黎智英資助香港的民主活動了。由此可見,即使以往美國表態支持香港回歸,但它只要有空子就會鑽,不會錯過任何機會。
俄羅斯早就對北約及歐盟東擴起戒心,但要到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及其他顏色革命爆發後,才清楚美國葫蘆裏賣甚麼藥。2008年,北約考慮將格魯吉亞和 烏克蘭納入北約,其間普京已明確表示「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它將不復存在」,以表明他的決心,可是北約仍聲明兩國將加入,這直接導致了同年的俄羅斯——格 魯吉亞戰爭。
之不過,格魯吉亞的戰敗及其兩大片土地被割,並沒有令北約公開聲明放棄納入格魯吉亞及烏克蘭,北約反而在翌年繼續東擴,將阿爾巴尼亞及克羅地亞納入陣營。 北約的擴張,連圍堵政策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也看不過眼,指「是個可悲的錯誤,根本沒有理由這樣做」。
換言之,俄羅斯已多次警告美國,美國就是不聽,這也是為何米氏認為普京往後的行為,包括佔領克里米亞,純粹是防守性,而非攻擊性的主要理據。事實上,2月 的烏克蘭革命,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是經合法渠道取得政權的,但美國與歐盟卻煽動烏克蘭反對派,以非法手段推翻亞努科維奇,你說普京怎會不光火?這與香港開 始有人拒絕認同「少數服從多數」,主張公民抗命,程度有差異,但本質上是相同的。
愛挑撥離間 出事後袖手旁觀
再者,美國在革命中的介入是明顯的:紐蘭與美國前總統候選人,現任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竟親自參加了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大家可想像他們來港參與示威)!
革命發生後,副總統拜登不忘鼓勵一眾烏國議員,說「這是達成原來橙色革命目標的第二次機會」。中情局局長亦連忙提升與烏政府的安全合作,這些毫無疑問是西方的挑釁性舉措,但可恥的是,美國心知自己鞭長莫及,根本沒有意思出兵支援烏克蘭。
「真普選」若到手 港撕裂更容易
簡單來說,在格魯吉亞、烏克蘭或香港也好,美國就是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引誘和挑撥他們的反對派領袖和人民,即使他們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亦然,這在任何有直選的地方也幾乎必定會成功——故取得所謂「真普選」,反而會令香港更易走上烏克蘭的撕裂之路。
此外,不難發現美國其實最喜歡用反對派自己的損失(如普選),來挑起他們對目標對象(俄羅斯/中國)的敵意和怒火,但到出問題時,她卻不會理你的死活——如格魯吉亞因戰爭而兩地被割,西方卻連手指頭也沒有動一下;烏克蘭丟失了克里米亞,情況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目前美國在香港所採用的「非暴力鬥爭」這一套卻更卑劣:美國連錢也不願多花,要反對派自己動手,令美國毋須親自介入,變相叫他們自生自滅,如果見勢色不對就改打持久戰,搞「不合作運動」,她自己則靜觀其變。
話說回來,雖然中央對香港普選的國家安全憂慮完全成立,但筆者也認為,將普選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鈎,對港人來說很難接受:一則中央在普選問題上已應允了港 人,二則是大多數港人仍未習慣以此角度思考問題。之不過,「國家安全」這層面的考慮,在「後佔中」時代必然會繼續存在,港人對此必須有更深刻的理解,不要 奢望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